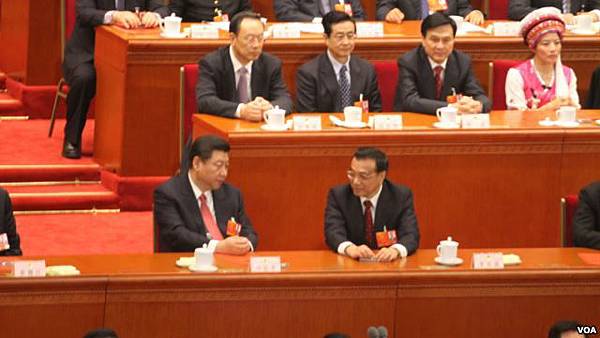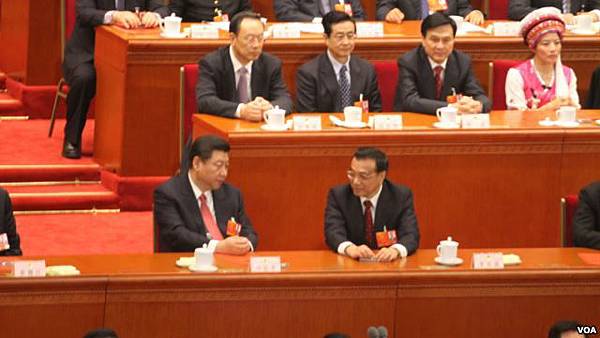——何清漣:習近平:中共政治制度的奴隸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9日起一連4天在北京召開,目前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寄予厚望的三中全會注定在大動盪中開幕。(大紀元合成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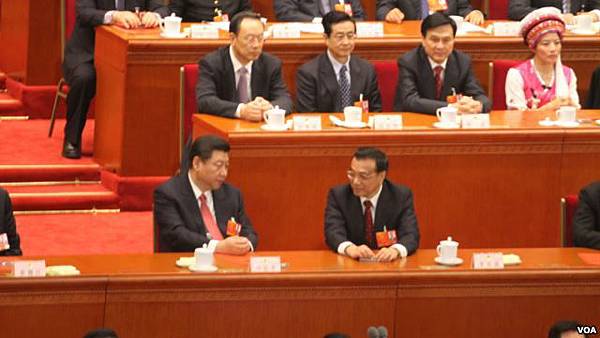
習近平(左)在主席台上和李克強交談(美國之音東方拍攝)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事前並未釋放任何政改信號,但海外媒體還是從毛語錄中止發行、習未去韶山朝拜毛故居等行跡去推測習近平的政治動向。一些對習近平原來充滿期待的人認為,習總書記上任一年多以來沒找到方向,政治態度左右搖擺,既得罪左派、又得罪右派,還得罪了太子黨——這句判斷乍聽之下,彷彿習近平在朝野樹了不少敵。這話的前提是錯將崇拜權力的專制政治當作民主政治,以為統治集團內部的不滿者有機會成為與習近平抗衡的政敵。
誰是習近平的政治強敵?
主張憲政的自由派(即中國習稱的“右派”)本來就被中共強力壓制,習近平打壓他們,無所謂“得罪”不“得罪”。左派本來就媚權,過去數年在鬧騰得太歡暢之時,當局也不是沒打壓過;但左派也不以為這是當局“得罪”他們,過段時期自會調整方向,少說當局不愛聽的話,就可以復出了。現在,雖然薄熙來已被監禁,烏有之鄉卻繼續辦下去,只要繼續罵普世價值、民主憲政與外國資本等反華勢力,左派就覺得自己還有用武之地,會主動親近黨中央與習總書記。三種勢力當中,只有太子黨是否擁護習近平關係到京城政治——相當於封建王朝的親貴政治,這政治的工夫不在檯面上。但開國元老們在世時,京城政治在某些關鍵時期,甚至可以左右最高當局的政治選擇,比如1978年。
應該說,太子黨——寬泛一點說是“紅二代”,太子黨只是其中級別高的元老後裔——是否擁護習近平,現在已不是問題了。最近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算是個標誌性事件,“紅二代”已經通過踴躍出席該座談會,向習總書記表示臣服;就算還有人不服,那也只能是“腹誹”了。習仲勛的紀念活動因為是由習遠平出面籌辦,因此算是亦私亦公,公私兼顧。因是當朝天子之父,各地政府“自發”的紀念活動當然不少,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紀念會主場參加者規格自然很高,各元老子弟(包括薄熙來的盟友)紛紛出席這一紀念活動,以此表明自己對新君的忠順。由於一個家族只有一位代表,未能與會的“紅二代”成員還表示遺憾。
通過這一紀念活動,習近平展示了他的強勢地位:他擁有了江澤民、胡錦濤從未真正擁有的說一不二的地位,黨內已經沒有任何人敢公開挑戰他的個人權威了。從此,習近平的個人專斷將代替胡錦濤時代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遙想當年鄧小平垂簾聽政時期,還有個資格相侔的陳雲時時掣肘,如今政治局常委內還有誰敢不賓服?
“紅二代”當中,習近平算是最年輕的成員。再過幾年,目前還在政軍財界任職的紅二代都將年逾七旬,這個京城親貴圈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力將隨着他們的相繼離職辭世而日漸弱化。“紅三代”目前剛在政治起跑線即縣處上開跑,離省部級還有一段長征路。紅二代要想讓紅三代順利接班,並繼續發揮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不僅不能與習近平做對,還得恭順地奉其為“紅二代”的政治代表。
習近平之敵:制度生產的腐敗官僚集團
習近平這一年內的政治動靜確實不斷,每次都有分析者從中找到其左右轉舵的跡象。我從不這樣分析習的政治動向,所謂“中國夢”主訴仍然是富國強兵,與毛鄧並無不同;清除“精神污染”、統一輿論口徑和“毛式”思想整風運動等,主要是針對西方和平演變策略而發,目的是維護中共一黨專政;“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則是針對官僚集團的嚴重腐敗,所有這些,只說明一點,習近平想用毛式鐵腕統治維護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
但是,在太子黨及紅二代心目中,應該享受裙帶資本主義的權貴,本不應包括平民出身的官僚。這一點不會被黨報黨刊宣之於口,但自胡溫第二任期開始,在紅二代十分活躍的京城政治中,這情緒表露得越來越明顯。2010年3-4月間,英國《金融時報》曾連發“生而為錢的中國太子黨”等幾篇文章,談到這一點,其中那篇“新生代‘太子黨’”(Red-blooded' veterans versus ruthless arrivistes)非常清楚地指出新老太子黨的矛盾:“太子黨”一詞原本是特指中共革命高級領導人的子女——他們的父輩要麼是與毛澤東一起參加過傳說中的長征,要麼是1949年革命勝利時核心領導班子的成員。近幾代“技術派”領導人(江胡兩代)的後代是新太子黨,他們壟斷了點石成金的中國私募股權行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上世紀90年代初為了鞏固權力,曾逮捕數位與鄧小平子女關係密切的商界人士,並關閉了他們的公司。
該文還指出,“出身於革命世家的老太子黨們十分真切地覺得,這個國家是屬於他們的”,“一旦閹人得勢,離政權滅亡也就不遠了。”( when the eunuchs become powerful it means the end of the dynasty is near.")寫這些報道的記者明確指出,上述信息是京城圈內的消息人士提供。這點我相信,因為只有那個圈的人,才會如此藐視技術官僚出身的當政者。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此次習仲勛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中,許多革命世家的紅二代們受邀出席,包括早就被毛清除的高崗遺孀及其兒子在內,都被習當作“自家人”,但媒體卻沒有報道有新太子黨成員受邀出席的消息——如果有,香港媒體應該不會遺漏。
《南方人物周刊》11月6日發表“陳小魯紅二代光譜”,被採訪的有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馬文瑞之女馬曉力,後者近年以習家世交身份,成為“紅二代”當中的活躍代表人物。他們都明確地表達了紅二代的精神認同:紅色江山萬萬代,“紅色江山不能敗在我們手裡頭”。《金融時報》談的是“新太子黨”,但在馬曉力口中已經成了“官二代”:“我們和官二代不一樣,一定要劃清界限!”“大部分紅二代沒什麼權,也沒什麼錢!”“我們也非常痛恨腐敗,非常痛恨飛揚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讓這些人把黨給糟蹋了”……
理解了“紅二代”內部的精神認同,就會理解習近平今後的執政任務是保護紅色政權不變顏色,絕對不能放棄共產黨一黨專政政體。反腐,主要是反官僚集團的腐敗,這也是保持中共“執政能力”的必要手段。過去中共其實也是這樣做的,以往十餘年裡落馬的幾十位省部級官員均出身平民,有些還是“苦孩子”。至於外界認為習近平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這種觀察流於皮相。我認為這是習近平想通過這種方式警告某派政治勢力:決定未來中國的政治路向是我的事情,誰也別想干擾。怎樣做,我心裡有數。誰也別想給點顏色就敢開染坊。
但是,京城政治只對高層政治起作用,各地政府畢竟是由平民出身的官僚集團在管理。這些官僚對中共政權並無“紅二代”這種血肉相連的感情,更多地是衝著利益二字入黨做官,而且還要做“裸官”。因此,習近平如何駕馭這駕早已經被腐敗嚴重鏽蝕的政治列車,是個問題。
可以歸結如下,習近平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源源不斷生產腐敗官僚的政治制度,而這政治制度,恰好是他與“紅二代”都要極力保衛的紅色政權。習近平無力改變這一龐大的官僚機器的運作慣性,他其實只是這一政治制度的奴隸。
轉自:【看中國2013年11月10日訊】

中共監獄迫害法輪功學員所實施的種種酷刑演示圖:老虎凳、暴力毒打、死人床(抻床,也稱五馬分屍)、電棍電擊、抻床、吊銬、灌食(鼻飼)、鐵椅子、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野蠻灌食、電棍毆打等。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那天,勞教所採取了「決裂也得決裂,不決裂也得決裂,非決裂不可;寫五書也得寫,不寫五書也得寫,非寫不可」的泯滅人性的殘酷手段。
據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九日報導,吉林松原市蔡國賢女士二零一一年七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勞教所,為了讓她轉化,勞教所採用了各種酷刑:辱罵、拳打腳踢、電棍電、每天站十七個半小時等,尤其是「抻刑」加電棍折磨十幾個小時後,令她生不如死。下面是她訴述的遭遇。
我叫蔡國賢,女,五十二歲,家住松原市長嶺縣永久鄉。二零一一年七月左右,我因在親屬的喜宴上贈送《明慧週報》和神韻晚會光碟,被長嶺縣公安局、永久鄉派出所警察從家中綁架。我被長嶺縣拘留所非法關押半個月後,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零七個多月(包括在勞教所被非法加期四十天)。
勞教所分幾個大隊,我被分到二大隊,我寫了三封復議信,送往松原市勞教委員會,依法要求他們撤銷對我勞教一年半的決定,無條件放我 回家,賠償我的一切損失。結果三封復議信一去石沉大海。我被非法關押在勞教所二大隊度過了有生以來最艱難痛苦的近十二個月(差五天一年)。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勞教所二大隊解體,我被轉到三大隊。由於我堅決不寫放棄信仰的所謂「五書」、並以思想匯報的形式把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直接交到獄警、大隊長那裏,到三大隊的當天,勞教所就把我和其他人隔離,關到單間——就是所謂的幫教組繼續迫害。以下是我被非法關押在三大隊期間遭迫害的情況:
大隊長說恐嚇:勞教所裡一百零八種刑
劉英(大隊長)說:這勞教所裡有一百零八種刑呢,咱們一點點嚐試,能讓你活著出去嗎?惡警強迫法輪功學員看誣蔑、抹黑大法和師父的電視光盤,包夾強迫給念歪曲、抹黑大法和師父的書聽。
強迫看聽。一個姓牛的小獄警,把我拽到離電視很近的地方,還往前拽,一下下的打我,葉炯(管教)到幫教組來,先是一下下用手打我,接著就是一腳一腳踢我,我往後退,她說「不許動。」扯著我的衣領,拽到她跟前繼續踢,一連踢了幾十腳。我說她迫害我,她說:「就迫害你,一月還拿四千多元工資!」
王雷(獄警)每次到幫教組來,都氣勢洶洶的拽著我說:「往前站、往前站!」強迫我寫甚麼感想(觀後感),因為我寫出來的東西都是在說法輪大法好、師父好,用正理駁倒他們的歪理。包夾看了之後說:「不行。大隊長(劉英)、王管教(王雷)她們不能收。」就給撕了。然後還強迫我寫。我寫的還是原來的事實,包夾看了,還說不行,還要給撕。我說:「不是讓我寫感想嗎?這是我的真實感想。等大隊長、管教她們來,我自己交給她們。」
葉炯(獄警)、劉英(大 隊長)到幫教組來看了我寫的感想,立即大怒,葉炯一連串打我嘴巴子,劉英對我拳打腳踢。說:「收了她的筆,不讓她寫!」她們發現轉化不了我,下午就強迫我站著。強迫我每天站十七個半小時,包括吃飯都得站著吃。中午大伙都休息時,我坐一會都不允許。一天中午我實在累的受不了了,就趁著看著我的包夾睡著時,拿 一把椅子趴在窗台上睡著了,歇一會。劉英來到幫教組(我呆的房間)看到了,在我身後踢到椅子上,把我嚇醒了,急忙站了起來。劉英邊打我耳光子、邊罵:誰讓 你坐下的?!你他媽給我好好站著!胡說甚麼站著是你自己的選擇!
葉炯(獄警)也曾經邊打我,邊指著我的鼻子問:「你是誰。」我堅定的說:「我是大法弟子。」她說:「那你就站著!」
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還特意把我叫到管教室打一頓,威脅我必須好好站著。她們讓我寫,我寫出的東西能把她們的歪理駁倒,沒有她們要聽要看的,達不到 她們讓我寫五書的目的,她們就強詞奪理。一次,劉英指著「天安門自焚」的偽火片,讓我看這、讓我看那的。我說:「都是謊言,都是欺騙。」王雷(獄警)照著 我的前胸就是兩拳,打的我半天才上來一口氣;劉英跑過來打我幾個大嘴巴子。一天劉英、王雷、葉炯、另外一個大隊長(江大隊)好像也在,還有兩個包夾,我在 那站著,他們坐著,七嘴八舌的衝著我,時不時的跑過來打我幾下踢我幾腳,似乎要把我活活吃掉的樣子。
為了得到五書,他們使用的手段很卑鄙也很殘忍。一天在幫教組(我呆的單間)劉英(大隊長)、王雷(獄警)、葉炯(管教)加上兩個包夾,她們七嘴八舌的這麼讓我決裂,那麼讓我寫五書的。無論她們 怎麼說,結果都是我說的話把她們說的話駁倒。她們沒有理由說服我,就想使壞,葉炯說:「等會我上走廊喊去,告訴各小隊的人,我就說蔡國賢決裂了,寫五書 了。」我說:「誰也不能做那傷天害理的事。」她不吱聲了,也沒敢那麼做。
兩個包夾吃完中午飯回來,其中一個包夾跟我說:「我給你寫五書了,都是現成的,抄上就行。」我說:「(前)總理是李鵬,重名重姓的人多了,他說他是總理也不好使啊。」包夾不吱聲了,沒有那麼做。
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二人對我這個每天被強迫站半個小時、身體被糟蹋的不成樣子的五十一歲的婦女踢來打去的,在他們二人身上看不到女人那種膽小溫柔的形象,打起人來既凶殘又狠毒,用大拳頭啪啪的打我的腦袋,兩個人一人一根電棍電我,我的手剛下意識的去推劉英拿電棍的那只胳膊,劉英說:「你挨著我就算襲警。」劉英拿出一本師父的《大圓滿圖解》衝著我說:「你師父怎麼說的、怎麼說的,你看看。」我說:「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超越法律了,憲法規定,信仰自由。」劉英把《大圓滿圖解》經書摔到地上,用雙腳踩著師父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去搶她踩在腳下的經書和師父的照片,她一動不動,我沒搶下來。葉炯誘騙我說: 「你快說『我決裂了!寫五書!』我們把你師父照片撿起來貼牆上。」她們二人一邊打我,一邊胡言亂語。從中午休息獄警開始上班後,把我叫到管教室打,一直打到她們快要下班時。
每天吃完中午飯,葉炯(管教)來換兩個包夾回監室睡覺。她在那看著我繼續站著,不許動一點。(只要寫決裂書、五書就不用站著)給我放污蔑法輪功的光盤,就是勞教所裡說的所謂的學習。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裏時刻想著「法輪大法好」。晚上大伙都睡覺的時候,讓我從幫教組出 來,換另一個房間。在一個沒有人睡覺的監室裡站著,繼續站到十一點。因為換這個房間有床,兩個包夾能換班躺在床上睡覺休息。
站到二十幾天之後,腳和腿腫痛的不敢走路。一個「護廊」看見我來回上衛生間走路一瘸一拐的,腳腫的穿不上鞋,只能趿拉著,就給我找了一雙沒有人穿的大號鞋,讓我穿上了。 後來聽說,那個「護廊」因此還被大隊長罵了一頓。衛生所大夫到樓上看了我的腿和腳之後,讓我吃藥。我說:「不用,我這是硬站著累的。」大夫說:「那你就坐 兩天(幾天),歇歇吧。」情況還是即使有椅子也不讓我坐,王雷(獄警)讓我坐一個「蹲、蹲不下,坐、坐不下」的小塑料花盆。趁我不在屋時,把我的棉墊也扔 了,不讓我坐,依然是坐花盆十七個小時,不讓動。
就這樣我又坐了二十多天的小塑料花盆,大約是九月十日左右的一天,王雷(獄警)到幫教組 (封閉我的單間),沒好氣的對我說:「光看電視不行!得想事兒!」她嘴裡的「想事兒」就是想「決裂」的事。我和往常一樣回答她:「不想,沒甚麼可想的。」 無論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或者是其他甚麼人跟我說讓我「想事兒」——想「決裂」的事時,我也都是這麼告訴她們的,就是「不想,沒甚麼想的。」王雷 就說我頂撞她了,把我叫到管教室。劉英、葉炯她們二人手裡各拿一根電棍電我,我往後退,她們二人截著,中間夾雜著一陣陣的拳打腳踢、打大嘴巴子、大脖摑 子。劉英抓著我的頭髮打,薅掉一大團頭髮(當時不知道,回到幫教組後,包夾對我說:「你的頭髮咋高高靿靿的」,摘下來一大團抓亂薅掉的頭髮)。
午休後,獄警上班,我又被叫到管教室打,被電棍電。一直到快要下班時,才讓我回去。罵著:「滾回去!」沒好氣的把我從管教室推出來。葉炯(獄警)跟 著我回到幫教組(封閉的單間),讓我面壁站著,我的腳都緊挨著牆根了,葉炯還一直說:「往前站、往前站……」一腳一腳地踢我穿單褲的腿。之後還對我非法加期五天。
我被強製麵壁站了十多天,又讓我站著幹活,和其他人一樣多的任務。因為都是做各種各樣的手拎兜和食品盒,其他人都坐著干。又過了兩 天,我跟管活的大隊長江麗君說:「我站著本來就比幹活累多少倍,還跟大夥一樣幹活,讓我坐著干吧。」江大隊長說:「中午你可以坐一會。獄警上班不行。這我 還沒和人家商量呢。」王雷等人知道我中午坐一會是江大隊的意思,也就不好不讓我坐一會。但是王雷多次把兩個包夾叫到走廊裡,安排兩個包夾,獄警下班之後到 晚上十一點這段時間,我就是幹活也必須得站著,坐著不行,讓兩個包夾好好看著我。
從七月二十四日二大隊解散,我被分到三大隊,到九月三十日「十一」放假,我經歷了「打罵、拳打腳踢、電棍電、每天站十七個半小時(早五點半——晚十一點)、包括坐小塑料花盆硌屁股、包括面壁站著、包括站十七個半小時跟其他人干一樣的活的任務,共六十七天。
十幾個小時的抻刑折磨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那天,勞教所採取了「決裂也得決裂,不決裂也得決裂,非決裂不可;寫五書也得寫,不寫五書也得寫,非寫不可」的泯滅人性的殘酷手段。
剛吃完早飯,葉炯(獄警)把我叫到管教室,但不是獄警上班辦公的房間,是管教放穿衣櫃的一個房間,在兩個管教室的最裡面,也是最左面。和兩個管教室並排三個 門,右面是學員區(就是勞教人員),共十七個房間,中間隔著一道鐵柵欄(鐵門),鐵柵欄的左面是獄警在管教室的門外面坐崗的地方,鐵柵欄的右面是學員區的 一條十七個房間那麼長的大走廊。十八日那天,她們怕學員區的人聽到我驚天動地的哭喊聲,在管教室的門外,鐵柵欄的左面(管教區)獄警坐崗的桌子上放了一天半宿的錄音機。
十八日那天早飯後,我正在單間裡幹活,葉炯(獄警)來叫我到管教室來一趟。把我領到管教室,準確的說不是管教室,是獄警區內 管教室左邊的一個獄警放穿衣櫃的房間。葉炯(管教)怒氣沖沖的問我:「誰讓你坐下的?!」我說:「是江隊讓我坐下的,大隊長讓我坐下的。我站六十七天,每天站十七個半小時。」葉炯說:「大隊長還讓你決裂呢!你怎麼不決裂呢?!來吧,上床!」我心想:這次她們是不是想讓我上死人床,我在外面聽說過。她們七手八腳的把我的兩個手腕子和兩個腳脖子綁上,分別吊到一個事先準備好的一個單人床的上下鋪的四個角上抻。
參與(迫害)綁我的人是: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王雷(管教)、賈獄警、劉管教、還有兩個社會幫教,但這兩個社會幫教沒參與綁我,她們是聽 到我的哭喊聲從樓下(一大隊)上來的。她們勸我信佛吧,信佛吧……就是讓我信仰佛教。在吊我的床旁邊放佛教裡面的甚麼大悲咒音樂。她們誣蔑、辱罵法輪功。
「停止迫害吧!停止迫害!」我被折磨的哭喊聲驚天動地。她們就用毛巾捂我的嘴,用膠布一層層的封我的嘴,用布一層層的勒我的嘴。反反覆覆。毛巾掉了再捂,膠布 掉了再膠,勒嘴的布掉了再重勒。獄警快要下班回家的時候,賈管教還拿著電棍電我吊在床上動不了的腳底板子,讓我快點決裂、寫五書。劉英(大隊長)肥胖的身 體還多次坐到我在空中抻著的身體的肚子上,制止我哭喊。獄警是三點下班,管教下班之前她就好幾次坐到我的肚子上,一直到晚上八點來鐘,她多次這樣做。
獄警下班之後,每天都有兩個管教值班,十八日那天晚上是一個姓壬(音)的獄警和一個姓張的管教值的班,劉英,葉炯,因為我被吊一天不決裂,特意加的班。
屈辱
從早上八點鐘獄警上班到晚上八點來鐘的時候,十幾個小時的酷刑折磨,我身體承受不住了。大約晚八點來鍾時,她們錄完音,才給我松的綁。讓我在床上緩緩醒了一會,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兩個社會幫教(這兩個社會幫教是勞教所每天二百元錢請來的),四個人把我從床上弄起來,扶到一張靠窗戶的桌子 前坐下,葉炯(獄警)坐在我的對面,整個過程葉炯(管教)說一句,我寫一句,她咋說,我咋寫的,全是謊言。
我被酷刑折磨十幾個小時,兩隻手和兩隻腳腫的跟饅頭一樣,因為長時間不過血,又青又黑的。臉上汗水和淚水交織在一起。出汗把頭髮都濕透了,再加上用布條勒我的嘴的時候,是在後腦杓繞一圈過來的,反反覆覆,頭髮亂蓬蓬的。她們怕別人看到,當天晚上沒有讓我回監室睡覺。就在迫害我的管教室裡,就睡在迫害我的這張床的下鋪,還用手銬把我的手銬在床上。第二天早上,趁大伙都下樓吃飯的時候,葉炯(獄警)才叫包夾把我領回去洗漱,還特意讓我洗了頭。
第二天下午幫教組就換了一個房間,這個屋裡有幾張桌子和幾把椅子。靠南面窗戶的地方,有一張桌子和下面幾張桌子臉對著臉,兩個社會幫教講課給我一個人聽。屋裡面還有給兩個社會幫教助威的劉 英(大隊長)、王雷(獄警)、葉炯(管教)和兩個包夾等十來個人。她們威脅、恐嚇我:「不好好聽課、不好好學習,就讓你再次上床!」還讓兩個包夾把上一天吊我十幾個小時的那張床從管教室隔一道大鐵門和十幾個房間抬來了。見我稍有怠慢,劉英(大隊長)、葉炯(獄警)就對我拳打腳踢、打嘴巴子。她們強迫我聽幫教講的那些謊言,之後強迫我說。
幫教講完之後,還強迫我寫甚麼感想。我就把她們講的東西寫下來了,都是不著邊際的胡言亂語。我寫完。社會幫 教說:「拿過來我看看。」看完大怒:「啊!你寫這東西這是甚麼感想嗎?!這是甚麼感想啊?!這不全是我說的、我講的嗎?!」第二天就不讓我寫了。她們給我 放誣蔑法輪功的光盤看,邊放光盤,兩個社會幫教邊指著電視畫面誣蔑法輪功,之後讓我說。我說:「對呀,大法弟子做的對呀。你報導的東西歪曲了、誣蔑了法輪 功,大法弟子站出來說話,講清真相,對呀。」在場的劉英(大隊長)、葉炯(管教)立即衝上來對我拳打腳踢,王雷(獄警)坐在我桌子的對面,立即站起來一連 串打了我十幾個大嘴巴子。
到獄警下班時,幫教也下樓吃飯去了。我桌子上放著所謂的感想當幌子給包夾看,心裏想著怎樣寫嚴正聲明——聲明五書 是勞教所酷刑迫害,我全盤否定,不承認以及十八日那天被迫害的過程和聲明寫在一起。剛寫了兩行小字,身後的門開了。我急忙揣上衣兜裡,卻還是被社會幫教從 衣兜裡掏出來搶去了。那個歲數大的拿到手裡一看,說:「啊!這字這麼小我也看不清。」那個歲數小的接過去念:「床上鋪的四個角上分別吊著我的兩隻手和兩隻 腳。驚天動地的哭喊聲,『停止迫害吧,停止迫害』。她們就用毛巾捂嘴,用膠布膠嘴,用布一層層的勒嘴。」那個歲數大的怒氣沖沖的問我:「你到底想怎麼 地?!你想讓誰給你往外捎?!誰是你的親戚?!」我不慌不忙的說:「我想寫一篇日記,把十八日那天記下來。」因為當時這兩個社會幫教都在場,她倆就都不吱聲了。
第二天,獄警上班的時間,可能這兩個社會幫教把從我這搶去的那張紙上的兩行字給大隊長和管教看了。她們的態度都變了,不像原來那樣囂 張了。兩個社會幫教知道轉化不了我,她們動不了我的心,她們講的那些東西我怎麼也不信。再以後就不專門給我所謂的「上課」了,只是走過程,一天到幫教組來 一、兩趟瞅瞅。每天上大教室給各小隊的人講課洗腦,也不叫我去聽了。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兩個社會幫教就走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上,賈獄警值班,特意把我叫到走廊,反反覆覆的,再三囑咐我說:「明天省六一零和局裡的人來考核。你就說……要不還得加期,你還走不了。我們希望你早點回 家。」第二天是聖誕節——十二月二十五日,賈獄警臨下班前,她把我叫到管教室,把她上一天晚上交代、囑咐我的話,又說了幾遍。我說:「我知道怎麼回答。她 怎麼問,我怎麼答。」賈獄警不放心地說:「不行,你就說法輪功是×教?」我堅定而鎮定的告訴她說:「不是。」賈管教怒氣沖沖的打了我幾個耳光子,旁邊的藏 獄警也跑過來對我大聲吼道:「啊!天天擱電棍禿嚕你,就好受了。」考核前,江大隊長(在樓上單間裡)囑咐我一遍,讓我按照她告訴我的說。劉英(大隊長)更 是囑咐再三,要我一定按照她告訴我的說。我都告訴她們,我說我知道咋說。考核是一個人一個人進屋考核的。到讓劉英(大隊長)領我進去的時候,屋裡有兩個考 核的人(哪個是六一零的,哪個是局裡的不知道),其中一個人指著一把椅子讓我坐下,先問了我是甚麼時候開始信法輪功的,以及寫沒寫五書等,接著說:「談談 吧。」我說:「不知道哪方面,你問吧,你咋問,我咋答。」他問我:法輪功是不是×教?我堅定的告訴他:不是。第二天早晨,賈獄警到幫教組(我呆的單間) 來,重重的打了我幾個耳光,罵我一頓。二零一三年一月,月末,外面又來考核了,這次考核:我說法輪大法好。用她們的話說:我沒過關,考的最不好。
在勞教所的人,每人胸前都帶一個小牌,上面寫著本人的姓名及入所(勞教所)時間和出所時間。分紅、黃、綠牌三種。紅牌是不認罪、不認錯的人帶的,沒有減期。 黃牌是認罪、認錯的人帶的,帶綠牌階段比帶黃牌階段期減的更多。我在勞教所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加四十天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 六日,一年半加期四十天,一直都帶紅牌。在勞教所裡,對於堅定修煉的大法弟子任意的打罵、侮辱,沒有人管。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份的一天,在一次糊包裝袋時,兩個包夾要上其它車間倒膠,不讓我一個人住屋,出房間又不能超過一米遠,我只好跟著。車間裡一個姓邢的小獄警大聲吼道:「蔡國賢!你出去!不許進屋!」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大約)二十九日那天,三大隊所有的人都到大教室裡考甚麼試,正在考試時,葉炯(獄警)從我身邊的過道路過,在我身後扒拉我一下說,讓我剪 剪頭髮,因為當時賈管教剛安排人給我剪完頭不到一週,我抬頭看看她說:「我才剪完五天。」她又說:「不行!還長!」我說:「我願意這麼長(喜歡這麼長)。」她大聲吼道:「你願意的事多了!你還願意不上勞教所來呢,你怎麼來了呢?!」不一會兒,她站在我身後的門口外邊叫我出去一趟。這個葉炯(獄警)每 次把我叫到管教室打我,都是這樣裝出一副仁慈的樣子說:「蔡國賢,你到管教室裡來一趟。」或者說「你出來一趟。」這次我當著三大隊各小隊人的面,當面揭穿 她,說「葉管教,你找我有事嗎?」她說:「上管教室去一趟。」我說:「有啥事你就在這說唄。上管教室我怕你打我。」她說上管教室去,就這樣一邊往管教室走,一邊大罵。一進管教室葉炯一邊罵著,一邊暴打我一頓大脖摑子、大嘴巴子,她對在管教室的其他四個獄警說:「誰來摁著她?」在幾分鐘內剪光我的頭髮,抓起一把頭髮從根剪,我頭頂上只剩下參差不齊的幾撮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份的一天,也是兩個包夾上小隊車間倒膠,一個姓牛的小獄警讓我在門口面壁站著。
勞教所解教的人回家時,都是獄警送出大門外,家裏人來接。而法輪功學員解教時,大部份都讓當地六一零、公安局、派出所的人來接,目的是更進一步迫害。而我也一樣,她們(勞教所)知道那五書是我全盤否定、不承認的東西,她們就讓我所在縣公安局的人來接我。但是縣公安局的人不來(我回家後才知道的),縣公安局給當地鎮政府、派出所打電話讓來接我。劉英(大隊長)還特意讓來接我的鎮政府、派出所、村政府的人到我呆的樓上來接我,還特意把整個三大隊的人都叫出來,在走廊裡排好隊、站好,劉英(大隊長)講的話,說甚麼:「蔡國賢今天解教,當地鎮政府、派出所的人來對接……」她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威脅我,另一方面是對其他人又是一種暗示的威脅。
雖然勞教所如此安排,但接我的人確實讓我回了家,我感慨眾生醒了。
【大紀元2013年11月10日訊】(責任編輯:張頓)

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社會正在「潰敗」,慢慢地爛掉,三中全會醫治不了這種病患。圖為11月8日中共三中全會期間,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巡邏。(Feng Li/Getty Images)11月9日,中共三中全會在中共高層博弈、分崩加劇,天怒人怨的不安中召開。中共三中全會會有何實質性進展,引發世界關注。外媒報導稱,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社會正在「潰敗」,三中全會醫治不了這種病患。
北京學者:中國社會是爛掉了
美國之音報導稱,中國人大教授周孝正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接觸的知識界人士對三中全會根本就不關心,他身邊這些知識份子根本就不談(三中全會)這事。
周孝正說,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提出了所謂中國社會「潰敗論」,現在的社會是爛掉了,所以叫潰敗。潰敗階段,大家『抬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對於改革大家就沒有甚麼信心了。貧富差距這麼大,官員越來越腐敗,看看社會上這些事情,包括北京這個污染,霧霾都成為常態了。
周孝正說,孫立平的話是對的,現在是潰敗,慢慢地爛掉。並說很多中國知識界人士贊同這種分析中國社會現狀的觀點,而「三中全會」醫治不了中國社會的這種疾患。
中國人大退休教授張同新對美國之音表示,西方輿論希望三中全會上看到中國有一個重大改變,這是不現實的,不會有根本性變化。
據法廣報導,外界普遍相信這次中共三中全會不會觸及政治改革問題,將把改革重心轉移到行政體制度。
中共改革方向與利益集團構成的障礙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中國有媒體紛紛宣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出台全面的改革方案,但許多經濟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對此持懷疑態度。以下是報導列出的一些會議後可能解決的問題和會遇到的障礙。
銀行存款保險。此舉將確保儲戶在銀行出現違約的情況下能不受或少受損失。障礙:國有大型銀行認為,此舉是為支持中小銀行而付出的又一個代價。
利率市場化。如果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可能促使銀行為吸存而競爭,並使消費者獲得更高回報。障礙:與前一個相同。
放鬆資本管制。上述兩項措施可能還會為政府放鬆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管制鋪平道路。障礙:反對者認為資本管制有助於中國度過像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難關。
地方政府借款。若放寬對地方政府的借債限制,中國地方政府或許可以為一些債務再融資。障礙:中央領導人擔心地方官員可能會肆意揮霍。
徵稅。若允許地方政府留下更多的稅收收入,可能有助於減少對賣地收入的依賴。障礙:中央政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對稅收收入的控制。
國有企業競爭。大型國企控制著從能源到銀行業和電信等重要行業。中國可能降低部份行業的准入門檻,以刺激競爭。障礙:可能會遭到國有企業及相關政府官員的強烈抵制。
上繳利潤。官員們還可能讓國企上交更多利潤,提高國企向政府上繳利潤的比例。障礙:國企的政治影響力。
戶籍改革。戶籍改革有望加速城鎮化進程。障礙:城市居民擔心農村居民的湧入會導致醫院和學校人滿為患。
土地改革。可能讓農民在出售或出租土地方面獲得更大的自由,使他們可能放棄土地,遷入城市。障礙:地方政府依靠征地賣地的權利增加收入。(責任編輯:林銳)
京城百姓談三中全會 學者提「潰敗論」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登場,北京核心地區明顯加強了安全警戒。面對滿街警察,有的北京民眾表示了複雜的心情。
目前,警察嚴陣以待,部份道路關閉,著裝公安,便衣警察,安全協理到處可見。除了天安門廣場警戒森嚴外,城區主要幹道,小街小巷也是如此。軍警駐足站崗,游動巡邏。
一位53歲的北京居民李女士對美聯社記者說,警察太多了。她說:「我還沒有覺得甚麼,就是覺得警察太多了,(反倒是)給人以不安全的感覺。」
北京居民王平更是抱怨高物價、高房價、高污染給中國普通民眾帶來的苦惱,加上三中全會召開使北京雞犬不寧。雖然參加三中全會的街頭保衛行動,但是自家並未在改革中真正受益。這位北京居民對美國之音說:「(對三中全會)不抱甚麼希望。甚麼中國夢啊?這個夢,那個夢,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
人大教授周孝正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接觸的知識界人士對三中全會根本就不關心:「我身邊這些知識份子根本就不談(三中全會)這事。我也沒有聽任何人說過。我想跟他們說,他們也不說。」
周孝正說,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提出了所謂中國社會「潰敗論」,並說很多中國知識界人士贊同這種分析中國社會現狀的觀點,而「三中全會」醫治不了中國社會的這種疾患。
他說:「清華大學有一個教授叫孫立平。他有一個觀點叫『潰敗』。現在的社會是爛掉了,所以叫潰敗。潰敗階段,大家『抬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對於改革大家就沒有甚麼信心了。貧富差距這麼大,官員越來越腐敗,看看社會上這些事情, 包括北京這個污染,霧霾都成為常態了。不颳風,肯定霧霾。孫立平的話是對的,現在是潰敗,慢慢地爛掉。」
報導說,為菜籃子著急的北京市民,以及「北漂」京城多年無錢買房、結婚苦惱的年輕人,更關心的是基本需求;同樣住在北京,好學校並非每個孩子都能進,高檔居民樓的燈光,照亮的只是別人家庭。地鐵內很多人每天往返好幾個小時上下班,但是不論怎麼奮鬥,好像都離夢想都越來越遠。
61歲的老北京居民邵文玉(音)說:「物價已經上天了,而我們是地上的人,是地上活著的人,要吃飯的,是要喝的,但是已經沒錢啦。」
大學四年級學生劉小姐:「現在大學畢業找工作很難,三中全會要是能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就好了!」銀行白領黃小姐:「希望樓價不要再漲了,最好降下來。還有物價也太高了,就是工資跟不上!」(責任編輯:胡宇龍)
【大紀元2013年11月10日訊】(combin post:kinghung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