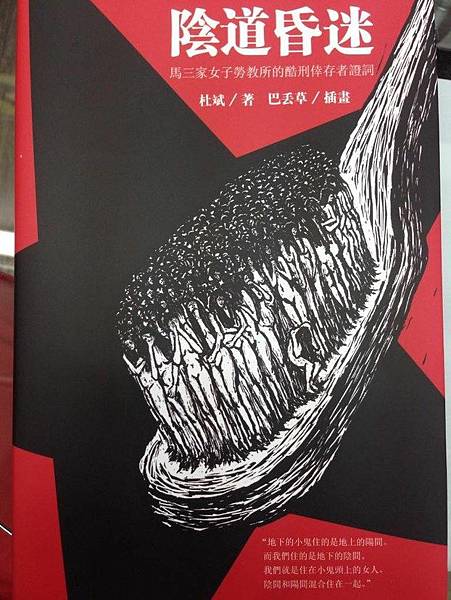
《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一書周一在香港上市。(封面照)
曾拍攝過揭秘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內幕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的導演杜斌,他出版的新書《陰道昏迷 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7月21日在香港上市。該書對數十位酷刑受害人和見證人進行了訪談。
杜斌在推特上寫道,「『我們是人,不是牲口』,正是基於這一點,才有了這本書。這本書是要銘記肩負繁衍人類的重任的女人們所遭遇到的無可言說的凌辱和悲劇。」
把手裡的東西全拿出來 讓外面世界知道
杜斌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外面的人知道這些事情不能發生在人的身上,因為我是一個人,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才會做,我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了。有一點必須要說出來的,我們是一個人,不是牲畜,不能想怎麼折磨我們就怎麼折磨我們。……我會把手裡的東西全部拿出來,要讓外面的世界知道,我們是人,不是牲口,中國政府不能這樣污辱我們人。」
杜斌的朋友、北京社會活動家胡佳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馬三家的受害者劉華最擔心的一點是,馬三家的姐妹們用陰道帶出來的在裡面寫下的馬三家暗無天日的情形有關的資料,貼在一張舊報紙上,留在杜斌那裏,很怕被警方抄走。馬三家的血淚史某種意義上是杜斌這本書的初稿,女性用私密的陰道帶出的資料以及杜斌寫的書,既是歷史的證據,也是歷史的證言。」
劉華已被摧殘得滿身是病,她曾經被扒光衣服電擊,她說:「有學員被電過乳房、陰道,還往陰道裡灌辣椒麵,上死人床;有學員被電棍插到陰道裡;有學員褲子被脫光,用棉簽往他小便處戳。」
朱桂芹說:「把我綁在死人床上,兩腿八字形拔開,把我的外褲、內褲都脫到膝蓋以下,上面灌食,下邊倒尿灌腸,大小號都不讓,造成我婦科炎症,拿棉簽捅我陰道下邊,慘無人道。把我關到法輪功小號,這個小號可曝光到國際社會,可以看清中共迫害法輪功到甚麼程度。」
另外,杜斌還拍攝過一部揭秘馬三家女子勞教所酷刑迫害法輪功學員及上訪者內幕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該片已於2013年5月1日在全球網絡公映。
杜斌在2011年三月還出版了一本題為《牙刷》的後現代詩歌體小說,作品隱喻1999年中共對法輪功發起的迫害。《牙刷》描寫在監獄裡,獄卒用牙刷插入女性囚犯的陰道這樣一種滅絕人倫的酷刑。這種酷刑正是法輪功學員向國際社會曝光的酷刑。
杜斌表示:「發生在馬三家女子勞教所裡面的事情,如果真的要揭開來的話,我想中共政府將無法面對這個事實。因為發生在裡面的事情,就是反人類的事情。」
馬三家女子勞教所使用電擊、「老虎凳」、「死人床」、上「大掛」等酷刑迫害關押人員的真相一直被中共封鎖。
「我做了每個人都應該做的,那就是講真話」
杜斌的多本書籍,由於揭露了中共罪惡,不可能在大陸出版,因此在香港等地出版後,非常熱銷。2013年6月1日,因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以及出版新書《天安門屠殺》,杜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抓捕,北京豐台國保直接參與抓捕。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犯罪,在任何時候,審訊我的時候我也很坦然。」他說:「我做了每個人都應該做的,那就是講真話。」
杜斌說,當局反覆問他為甚麼要拍攝和寫書,是不是有人組織和授意?但杜斌就堅持自己做一個人的本份,「我就說因為我是一個人,我就是本著一個做人的本份,我當時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爺們。我對發生在女人身上的酷刑、虐待,我不能接受。是一個爺們都不能接受的。」
當局審訊他時,以他沒有親眼目睹酷刑為由,質疑為何敢指控酷刑,但杜斌表示,有關馬三家的揭露,最早是《視覺》雜誌4月7日披露,他的紀錄片在5月才發表,而且是真人實據,「他們問我有沒有見過酷刑,我說這些酷刑是對女人的,我是男人,怎麼可以看到?我採訪了十幾個受害者,她們都是不同時期進去的,她們關在不同的房間裡面被虐待,她們講述的,證明裡面確實有這樣的事情,如果你們覺得是虛構的話,她們可以給我作證。」
2013年4月7日晚,大陸媒體《Lens視覺雜誌》的「走出馬三家」的報導,以《還原女子勞教所真實生態:坐老虎凳 縛死人床》或《揭秘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坐老虎凳綁死人床強制孕婦勞動》等標題被轉載,是大陸媒體少有的碰觸中共禁忌。
強姦輪姦頻繁 「那裏面的情景是想像不到的邪惡。」
過去十幾年來,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一直是中共標榜為迫害法輪功的先進,以殘酷迫害法輪功而出名。
大量有關馬三家邪惡的真相仍被掩蓋,其中包括2000年10月馬三家發生的性侵害事件,震驚世界。當時有18名女法輪功學員被剝光衣服投入男牢房慘遭蹂躪,之後這一瘋狂惡行被其他勞教所及監獄效仿。
聯合國「婦女暴力」監察專員2001年度報告寫道:在1999年10月,1,5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拘留在遼寧省馬三家勞改所。學員們被強迫放棄修煉法輪大法,拒絕的人遭到身體的摧殘,被電棍電擊、被關禁閉,和被強迫做繁重的體力勞動。女學員的胸部和陰部遭電棍電擊。
2000年10月,馬三家發生了另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18名女性法輪功學員被扒光衣服後強行投入男牢房。有人目睹幾個犯人直衝年輕姑娘去了,事後沒有幾天其中一位姑娘就自殺,後來被救活。
據一位被關押在那的女學員對親友說,「那裏面的情景是想像不到的邪惡。」
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講述,馬三家惡警還叫囂:「甚麼是忍?『忍』就是把你強姦了都不允許上告!」
2001 年4月,被劫持在一大隊的法輪功學員鄒桂榮(被迫害致死)、蘇菊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含冤離世)、尹麗萍(下肢癱瘓,一度精神失常)、周敏、王麗、周艷 波、任冬梅(未婚)、趙素環等九人,先後被馬三家送到張士男子勞教院,與四、五十個男人關押在一起受盡蹂躪和摧殘,有的女學員18天後精神失常。
對法輪功學員的性迫害成為馬三家普遍使用的邪惡手段。並且傳至全國各地的勞教所,強姦、輪姦等惡性事件頻發,大批法輪功學員遭此性虐待。而馬三家女二所所長蘇境當年因配合迫害法輪功得力而被司法部獎勵5萬元人民幣,還被評為所謂的「一級英雄」。
中國人權律師江天勇表示,這種存在的酷刑他們早就控訴過,只不過它太反人性、太殘酷、太陰毒了,對女性進行性虐待,比如用牙刷捅下體、用拖把戳下面……可以說世人覺得都不相信、難以置信。
除了對女性法輪功學員慘無人道的性虐待,對男性法輪功學員性迫害手法形形色色,根據男性生理特點,電擊生殖器、捏睪丸、扯生殖器,用刷把、笤帚把往肛門插……,令受刑者生不如死,許多人因此被折磨得昏死過去。
領導都是知情者、指揮者、參與者
江天勇披露,馬三家多種多樣的酷刑長期存在,而且領導都是知情者、指揮者、參與者。北京大興女子教養院、河北省女子勞教所、河北高陽勞教所、黑龍江前進勞教所、鄭州十八里河女子勞教所、湖北沙陽勞教所等等,裡面存在的全面酷刑,與馬三家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江天勇表示,對上訪者可以這樣做,那對法輪功只會更狠毒,只是國內媒體不敢報導,這些酷刑先用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然後再用在別的群體,所以說一個人沒有人權,所有人的人權都可能被踐踏。
馬三家是全國勞教所的樣板,也是縮影。據相關統計,像馬三家女子勞教所一樣的酷刑虐待和對在押人員的迫害,在大陸勞教所中相當普遍,數據顯示,大陸幾乎每一個勞教所都有多達數十種的酷刑,總體酷刑達上百種。
雖然大陸於去年底宣佈取消勞教制度,但一批勞教所被重新命名為「戒毒中心」,勞教制度仍以其他形式繼續存在。
天網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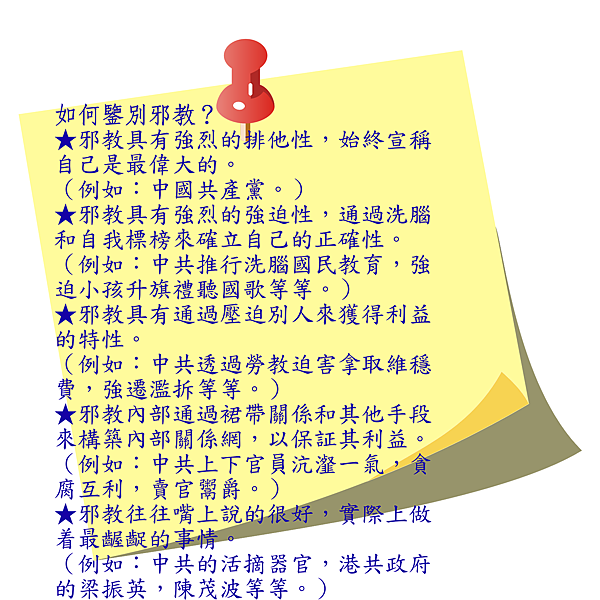
中共對號入座的邪教鑑別法。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